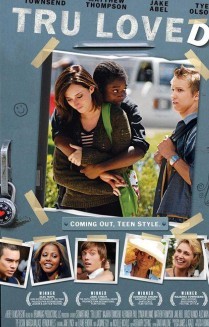计划出版一本旅行散文故事集——也是我的最后一本散文,之后只专注地写长篇小说。
这一篇也许你早已读过,会收录到这本计划中的散文集里。从2013年开始旅行、开始写,断断续续写到现在,我依然最喜欢这一篇。

把一个直男掰弯需要几个步骤?
在飞往深圳的飞机上,我闲极无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那个在深圳的好友已经为此努力了13年,并还在努力中。
好友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一起长大,在放学路上一人戴一只耳机像两人三足般保持步调一致地同听一盘磁带,然后我考来了北京,他复读了一年也考来了。
在大学里当我察觉自己其实喜欢男生后,我同时察觉了他也是——他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痞痞帅帅的,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他和我可以互相骂互相损大聊屎尿屁,但他在他面前,永远有一根神经紧绷着,不大声说话,亦不放肆胡闹。他喜欢那哥们主动逗他、调侃他、讽刺他,每到那时候,他就轻轻骂一句“傻逼”,然后自己嘿嘿傻笑。那哥们也在北京读大学,每个月当他提前花光了生活费,便会讪讪跑来好友的大学蹭吃蹭住几天。好友表现得好像他们是一对同乡异校的情侣:他来了,陪他吃饭,听他聊QQ上认识的女网友,在宿舍坐在他身旁看他打游戏,晚上睡一张床,他走时,从自己也不宽裕的生活费里拿出两百或三百元给他,百般嘱咐:求求你省着点用。
“你是真心喜欢他吧?”,等我上了大三并陷入一段深深的苦恋后,我问了好友这问题,以为将心比心。结果好友回我:“放你妈的屁,我只是从小就照顾他,成了习惯。”
爱上一个直男,把我的大学生涯搞得很惨,我眼见着他开始害怕我的歇斯底里或者不合时宜地表白而躲着我、眼见着他交了女朋友、眼见着我的情窦还没初开便碾落成泥,宿舍我是再也住不下去了,连课都不敢去上,想见他、更怕见他,于是大三那年,我在校外租了房子,像一只被嫌弃的鬼,幽幽地躲进自己的墓穴。
“我能借你的房子用用么?”,在我大四的某一天,好友打来电话,说他交了女朋友了,得办事儿。我问:“你确定么?”,他坚定地说:“必须的,我们宿舍就我没女朋友了。”我说没问题,然后铺了张新床单,放了几张A片在电脑旁,然后早早出门上自习去。大概过了5个小时候,他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进屋,我就恭喜他:可真能干啊!他抽着烟,对我说:“恭喜什么啊?没做成,硬不起来。姑娘气跑了”。我问,那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可能第一次紧张吧。
“还有呢?”
“你别问了”。他再不语。
没多久,我要毕业了,那哥们也毕业去了深圳。一起送走他后,好友对我说:“以前还不知道毕业能做什么,现在知道了,我也得往深圳去。”
“你干嘛不承认自己爱他?”
“我不敢,我怕我承认了,以后就更加心安理得了。你也知道那根本不是条走得通的路。”
我没对他说,我喜欢的那个人也去了深圳,但于我来说却是解脱,我到底是自私的,做不到不顾一切为谁奉献沉沦,既然连1%的可能都没有,我最好离他越远越好,我先于他提前离校,没有告别,连招呼也没打,就各分东西。我深信:所有当下你觉得深刻得会被自己带进棺材里的事,三五年也就云淡风轻了。哪有什么爱过的人会被认真地记住一辈子?尤其当你事后想起来,所有你和他的一切,都是自己跟自己玩儿时,你会忘得更快。
事实上,我的确做到了。毕业前三年全为生活挣扎,每天只想着怎么能在北京活下去,一周能有人请去酒吧喝一顿酒已经是最好的消遣。三年后,工作渐渐稳定,也有了房子,有了新的朋友和新的生活,接受命运安排,享受爱与被爱。几年后听同学说他在深圳结婚了,并发来婚宴照,当我看到照片里的他全然浮肿,胖得很符合一个普通女人身边一个老实丈夫的全部形象,我笑了——不是嘲笑,是觉得,这个人跟我早已没了关系。
但好友义无反顾去了深圳,哪怕成为那哥们身边狐朋狗友中的一员,他也认了。然后,我变成了他的秘密树洞,那些他对他永远不敢宣泄的情感,统统被他扔给了我。那哥们结婚他打电话来哭,那哥们媳妇生孩子他也哭,然后,那哥们继续找他借钱,他一边打电话来给我骂,一面又为那哥们添置了电视、冰箱、汽车,以及,那哥们媳妇的名牌包。每次我一开口劝他,他就匆匆把电话挂了,生怕我骂他。他也知道自己贱,但这跟吸毒是一回事,为了两分钟的快感,倾家荡产都可赔上,更何况不听劝。
他在深圳和那哥们一直死磕,嗑到那哥们都离婚了,他依然是那哥们身边被叫出去陪酒买单甚至支付嫖资的那位。但6年后,他28岁了。父母开始催婚,同事也给他介绍对象,他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要么坦率公开,要么就是死不结婚,千万别妥协,不然你祸害的不止你自己。
结果,他顶不住压力,和一个老乡迅速结婚了,并在一年后有了孩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无意发现他电脑里浏览同志网站的网页后,一发不可收拾地变得泼辣尖酸,她当然不会离婚,对生活的无能和对生活的绝望是两回事,对生活绝望了,往哪里看都是悬崖,跳下去才能一了百了,对生活无能,只会紧紧地抓住手边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哪怕握得粉碎。她诅咒他和他身边一切形迹可疑的男性朋友,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审问、讽刺,他变得消沉、抑郁,给我说不知道如何和老婆相处,再给我打电话,他总说:我羡慕你,敢敞开了活。
不然怎么样?只有这一辈子,责任那么多,快乐那么少。我要快乐。
这次去深圳,我以为他会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结果他来酒店找我,完全是一张喜气洋洋的脸。我开他玩笑,说:离婚了?他喝了一大杯酒,告诉我,和他终于有了进展,他不再排斥他的身体接触,有时候还可以亲一下,突然一下子就觉得生活好有希望。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能掰弯他?
80岁我也要等。

我在深圳还有一个朋友,在南澳做渔民,养殖海鲜。他以前是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和男友在一起12年。大概4年前,他男友因车祸去世,他在上海强撑了半年后,来对我们辞行,说:没有办法在这个城市呆了,每一条路、每一家餐厅、每一个地方,都有一起生活的气息。以前他在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是习惯,顺理成章的,他突然走了,发现这习惯能要活着的人的命。
我问:那为什么非要去南澳做渔民?
他说:不知道,就是冥冥之中想往那个方向走,我没那么冷艳高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做渔民也是一个好买卖。
在深圳的第二天,我去南澳找他,深圳那几天时而瓢泼大雨、时而雨过天晴。到了南澳码头,他在自己的渔船上等我,晒得黝黑粗糙,一见面就取笑我:你再穿干净点来啊!怎么不干脆穿香奈儿早春系列来啊!
妈蛋,你丫以前在上海是穿三件套的好么?!
我们坐他的渔船出海,他冰好了一箱啤酒,撬开了一盘子生蚝,说,吃吧,管够!我二话不说开始吃,他边喝啤酒边问我:你最近怎么了?
我答,心情不好,没大事儿。
他问,是稍微不好,还是已经不好到准备一起来南澳当渔民了?
我说,那还不至于,我多俗气的一个人啊。花花世界还没看够呢。
他笑笑,不问了。
我说,你别光问我?你现在怎么样了?是准备一辈子和右手过下去么?
他说,也没有,偶尔去香港转转,认识些新朋友,但好歹没合适的。心里放不下,你懂。
我问,那么久了?真有这么难么?
他答,你不懂,分手和突然抽身是两回事,分手是漫长的过程,你选择了放弃,从此他与你无关的生活画面将慢慢取代所有你们曾有的一切,然后你总有一天会发现,他已是陌生人了。但突然抽身不一样,突然抽身,还没有准备,那个人的音容笑貌就定格在了某一刻,再不会改变,留下的全是好的东西,而且只会随着时间愈发美化,想起来就痛。
我怔怔望着他,不知道说啥好,他一口气干掉一整瓶啤酒,哐当一下,突然跳进了海里。
我吓得发狂喊他的名字,赶紧去找救生圈,隔了一分钟,他才从水下冒出来,嘿嘿对我笑,说:快下来游泳!不然一会儿又要下雨了。
我一瓶啤酒砸向他,骂他:傻逼!你丫有本事就作死!
他大笑:我才不要死,我要好好的活,等你走了我就去香港见网友!
那时候,天空全是含满了水气的云朵,像一滴滴就要滑落的眼泪,终于在周遭最后一束光离场后,汹涌地坠下了。

我比他先去香港,在深圳停留了几日,我过海去了香港。打折季,和打鸡血是一个意思。
我在买一双鞋时,想起了曾经那个人,和他在一起时,他执拗地要踩我的每一双鞋,开玩笑:从此可以一直踩住你。
但结果呢?我只能说,先退出的那个人他妈的不是我!珍惜时连迷信亦是努力的方式,放弃了,转身各自去找下一双鞋踩,不过如此。谁会去验证当初许的愿下的咒是否真灵验?下一次灵验才最好!
所以,为了避免再被人踩住,买一双鞋还是自己先踩两脚,至少可以和自己不离不弃。
返京时,我分别收到了两个朋友的微信:
一条是:你要继续好好的,你活得开心,我这个做朋友的看着也开心,好像你替我活了一样。
另一条是:别担心我,预备66岁初吻。
我给他们回了同样的一条——
此刻不是永恒,不要画地为牢、不要为谁殉葬、不要心里暗示自己:最好的已经发生了。你值得快乐,是因为你一直在努力活着、在兢兢业业地做一个好人、一个靠谱的人,在明知事已无望却依然坚守情感或承诺,这一切都将被奖励,以你不会察觉的节奏或方式,或快或慢、或正中红心或柳暗花明,但总之,你不会困在这里太久。我相信并祝福,下一次见面,你已幸福了。
再会!